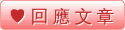|
2010-5-2 10:48
[論文寫作方式] 給國際法研究生的一封信—漫談論文寫作
| ||
|
|
|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