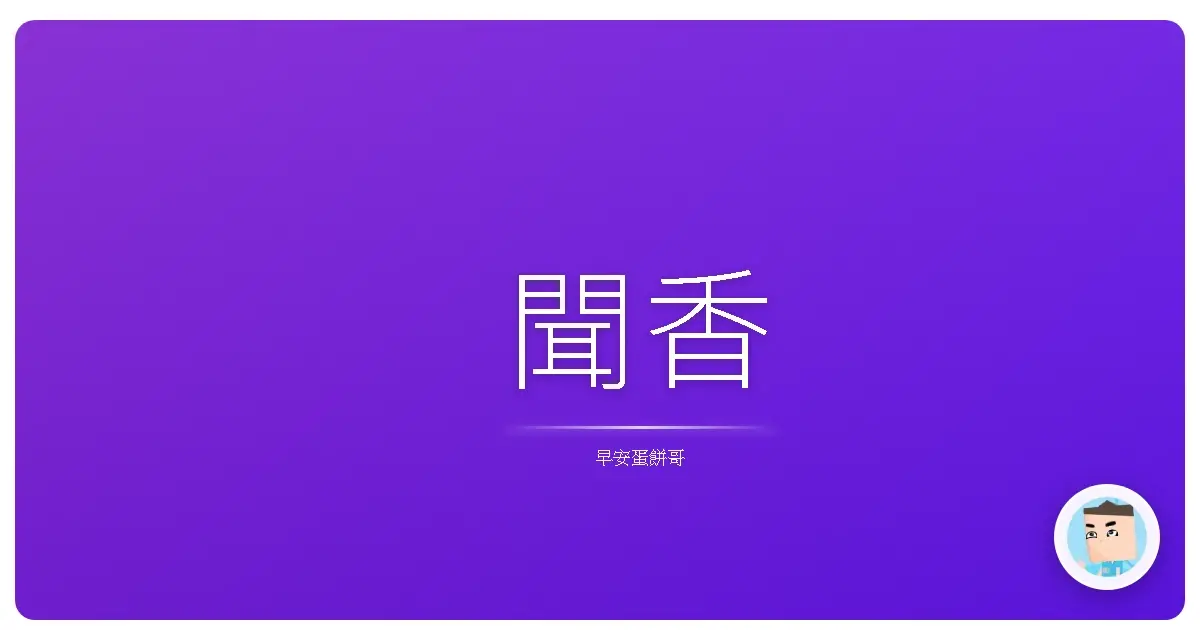
聞香
他叫Hy,一個名字是2個英文字母縮寫但鼻子靈得誇張的普通男孩。
不是什麼超能力,只是他真的,真的很會聞香。什麼花、什麼食物、甚至老師剛擦過白板殘留的化學味,他都能清楚分辨。不過最讓他心動的,還是那種淡淡的、帶點青草香又混著土壤清新的氣味——七里香。
說來奇怪,他第一次聞到這味道是在學校後門的破牆邊。一片廢棄角落,沒人打理,野草亂長,卻有一棵不知名的灌木,枝頭上開滿星星般的小白花。沒人知道那是什麼,只有他,每次路過都會忍不住吸一口氣。那味道像夏天才有的陽光,有點微熱、有點倔強,但又不刺鼻,像某種熟悉的回憶藏在某個午睡夢裡。
他後來偷偷查了,是七里香。
從那天起,Hy開始每天繞去那個角落。不說什麼話,也不做什麼事,就只是聞聞那花香。他說那是他「聞」來的祕密花園。其他人聽不懂,覺得他怪,但他從不解釋。
直到他聞出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。
有一次,班上那個總愛笑的男生韋勻,突然請假了整整一週。回來的時候還是笑,說是拉肚子,但Hy聞到了——那身上的味道,混著焦慮和泡過水的皮革味,那不是生病,是躲避。他後來才知道,韋勻的爸媽吵到快離婚,他被送去外婆家避風頭。
還有一次,校園圍牆內傳來七里香的花香,但那氣味裡多了一點金屬味、一點藥水味。他循著氣味走去,發現校工阿輝坐在樓梯間吸著氧氣瓶,臉色發青。阿輝有心臟病,發作了,沒人發現,是Hy衝去叫人救了他。
從那天起,他有了個奇怪的綽號:「香探」。
他不喜歡那名字,感覺太像某種香水廣告。但也沒人願意叫他什麼「氣味英雄」,畢竟他又沒飛天、也不會透視,最多就是能從味道裡嗅出些人心裡的碎碎念。
但七里香不只是花。對Hy來說,那味道是一種提醒。提醒他世界不是都香的,也有濕冷、也有霉味,但只要他還能分辨出那股乾淨的花香,那麼就還有值得期待的角落。
他後來開始偷偷種七里香。
一開始是在書包裡夾著枝條、葉子,然後在陽台種幾棵;後來乾脆拿到學校後門那塊空地,像秘密基地一樣,鋤草、灑水、拉管線。他不說理由,只說:「那邊太臭了,需要點香味。」
沒人阻止他,因為那地方本來就是校方不想管的死角。但神奇的是,自從那裡開了花、長了綠葉,很多人開始繞過去。有人坐著看書,有人在那裡打卡拍照,甚至有老師拿來當臨時講堂講生物課。
花香改變了一小塊地方,也改變了一點點人心。
但青春怎麼可能只有香味?
在他升上高二那年,一場意外打破了這一切。
那天午休,天空突然烏雲密布。氣象預報說午後雷陣雨,果然,一聲轟雷之後,雨勢如瀑布灌下來。有人跑,有人尖叫,有人乾脆躲回教室。但Hy不在教室,他跑去後門角落的七里香那裡,想拿回忘記收的澆水器。
然後他滑倒了。
不是普通的滑,是那種腳一打滑就直接撞上鐵管的痛。他倒在地上,雨水打在臉上,七里香在風裡搖晃,那味道變得苦澀、像裂縫裡流出來的回憶。
他腳踝扭傷,躺了兩週。
再回到學校的時候,那片他精心照顧的角落,已經被砍了一半。
學校說那是為了整修,要拓寬通道,不會全部拔掉,只是「整理整理」。但他知道,那些沒來得及開的花,全沒了。風一吹,連味道都淡了。
他那天沒說話,只坐在那裡,聞了很久很久。他想找回那熟悉的七里香,但怎麼聞都只剩雨後泥土的濕氣,混著施工的油漆味。
「你為什麼這麼在意?」一個聲音在他耳邊問。
是Tap,之前他們班的班長,對Hy來說,就是一個和他同班的女孩,不知道什麼時候走過來的,手上拿著一杯檸檬紅茶,還冒著涼涼的冷氣霧。
「只是花啊。」她說。
他搖搖頭。
「那是我能聞到世界還好的方式。」他低聲說。
她看了他一眼,笑了,「你太有詩意了啦。」
但她後來做了一件他沒想到的事。
第二天,他回到學校,發現自己的書桌上放著一小包東西,是密封袋,裡頭是一小撮七里香的乾花,還附著一張字條:「你說還好的方式,我幫你留一點。」
他聞了聞,那味道,還在。即使只是乾掉的花瓣,還是有那種倔強的清香。
那一刻,他突然覺得,香味也可以被傳遞。
他決定不放棄。
即使學校那塊地被改建了,他開始在社區、在附近空地、甚至學校辦公室前的花圃提案種七里香。他寫申請書、畫種植設計圖,還說服一堆不愛花的老師。
「我們不需要更多香味,這裡不臭啊。」有老師這樣說。
但他回:「我們需要一種能提醒人記得呼吸的香味。」
後來真的種起來了,而且比以前更多。他還辦了個活動叫「氣味記憶日」,邀大家來分享他們最難忘的味道。有人說是奶奶煮的滷肉香,有人說是初戀送的香水,也有人說是海邊的風味。
七里香,成了這一切的起點。
他不是什麼英雄,也不會飛。但他知道,他的鼻子,聞出了希望的方向。
七里香的氣味,就這樣悄悄從校園的角落,散進了更多人的生活裡。
一開始是社團活動,有個攝影社的學長想拍植物成長過程,結果拍上癮,每天下課蹲在花圃邊觀察七里香開花、凋謝、再重生。他說從沒想過一朵花能讓他那麼有耐心,「以前我連泡麵等三分鐘都覺得太久。」
然後是圖書館的那位總是戴著耳機的圖書股長怡恩。她原本不太理人,書借完就走,講話像開機器人模式。但有天她突然在班級群組裡發起一個奇怪的活動:「你覺得哪種氣味最能讓你靜下心來讀書?」
大家一開始以為她生病了,突然行為舉止這樣異常,直到有人問她為什麼問這種事,她只回一句:「我昨天在圖書館門口聞到一股像太陽一樣的花香,想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感覺到。」
就是那盆七里香。Hy特地種在圖書館入口的左側,說是「讓進來的人能先嗅到一點安心,再吸進書香味。」
他沒想到真的有人聞到了。
然後,一傳十,十傳百。
連校長都注意到了。有天校長突如其來地在早自習走進教室,全班嚇到站起來以為有人闖禍,結果校長手上拿著一盆七里香,說是「有人匿名寄來的一盆香氣」,放在辦公室三天後發現整個辦公室氣氛都變好了。
「我知道你們在搞什麼香探計畫。」校長盯著Hy,但嘴角止不住笑意。
「不是我啦。」他急忙撇清,但耳朵紅了。
「是誰不重要,我只想說,有時候學校需要一點,嗯……不只是分數的東西。」
說完他把盆栽留在教室,轉身走人,全班靜默三秒後爆笑。
這之後,香探計畫正式變成學校的非官方社團。沒有指導老師、沒有經費、沒有會旗,但有個LINE群組叫「鼻間記憶同好會」,還辦過一次「氣味盲測大挑戰」活動,讓同學用鼻子猜出瓶子裡的味道。有些是花,有些是香水,還有一瓶超臭的納豆,讓全場尖叫。
Hy發現,氣味真的會勾起情緒。有人聞到薰衣草會想哭,說是以前爸媽吵架後她媽媽最常點的香氛蠟燭;有人聞到巧克力味會露出笑容,說是暗戀的男生生日收到的第一份巧克力。
那味道會藏在腦袋的某個角落,等一點風吹過,就被拉了出來。
但不是所有回憶都香。
有一天,一個看起來很酷的轉學生出現在學校。男生叫陸北方,黑色T恤、灰外套、頭髮剪得像刺蝟一樣。第一眼看上去就讓人不太敢靠近,眼神總是漂來漂去,像誰都不想理。
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,只知道他是轉學來的,然後一直待在後排角落的位置。
Hy第一次注意到他,是在廁所外面。
那天他路過廁所,突然聞到一股熟悉的七里香,但味道中混雜著煙味。是一種很古怪的衝突感,就像陽光下燒掉的紙。
他往裡面一看,看到陸北方坐在廁所窗邊,手裡拿著一支未點燃的菸,靠在牆邊發呆。七里香的香味,是他外套上沾的。他也不知道怎麼沾上的,或許路過某處,或許……根本就是故意找來的?
那一刻,他沒開口,只是靜靜看了幾秒。
後來他偷偷把一張紙條塞進了陸北方的桌子抽屜,沒署名,只有一行字:「煙味會蓋住你身上的七里香。」
隔天早上,陸北方走進教室的時候,外套換了。
味道也沒了。
但他走過Hy座位時,輕輕放下一個透明瓶子——裡面裝的是七里香的乾花。
沒有一句話,但兩人像某種默契般,從那天起就成為了「不講話的朋友」。
後來的幾個月,他們會一起去花市買植物、研究種子、看氣象預測濕度,再安排澆水時間。還有人發現,學校角落每隔幾週就會多出一些香味不一樣的小花圃,有的像椰奶、有的像餅乾,據說那是Hy與陸北方一起設計的「氣味故事路線」。
每條路線都有名字,有一條叫「回家路上」,有一條叫「考試日的平靜」,還有一條叫「那年夏天」。
「氣味能替我們說話。」陸北方某天突然這樣說。
「因為有些話講出來太丟臉了。」他又補了一句,笑得有點像是放鬆。
他們沒說明確是什麼故事,但大家都知道,這些路線不只是花,它們記錄著一些沒辦法寫成日記的事。
就在這種香味包圍的日常裡,學期過了一半。
但生活總會來點試煉。
那年學校突發大型整修計畫,要把校園中庭打造成「多功能會議與表演中心」,那片原本種滿七里香和其他香草的空地首當其衝。
學生抗議沒用,校方說:「香味可以再種,空間不能浪費。」
Hy氣得不行,陸北方甚至想去發動靜坐抗議。但後來是Tap跳出來,用一種超理性又超感性的方式提出了一個解法:
「你們不是要蓋多功能會議中心嗎?那可不可以在設計裡納入一個香氣導覽走廊?」
她的理由是:研究證明,氣味能有效提升注意力、減低焦慮,對表演者與觀眾都有幫助。
還附了國外的案例佐證。那份報告厚厚一疊,看得校長都傻了。
最後竟然……真的成功爭取到保留一區七里香香氣走廊。
那一條走廊現在不只是香,也變成學校的打卡熱點,甚至有人開始用香味來寫作文、畫畫、作曲,說那是「記憶味道的靈感」。
……讓全場尖叫連連,結果笑到肚子痛的反而是那位一直自稱「味覺派」的男同學阿餅。他居然一臉淡定說:「這味道我阿嬤冰箱裡每天都有,聞起來像回家。」
活動結束後,「香探計畫」人氣直升,甚至有美術班的學生畫了一整面牆的七里香壁畫,上面還寫了一句話:「讓鼻子帶你找到心裡的風景。」這句話後來被印在了學校的畢業紀念冊封底,也不知道是誰提議的,但大家都覺得很可以。
而這些小小的改變,慢慢讓Hy意識到,他做的事情已經不再只是「讓自己能好好呼吸」,而是真的影響了別人。
但改變從來不只是順風而行。
某天,他在教務處門口聽到有人抱怨:「那什麼花啊?過敏都快死了!」還有人大聲說:「整天搞些有的沒的,學生不是該把心思放在功課上嗎?」
也對,有人不喜歡這種氣味。有些人過敏,有些人單純覺得麻煩。甚至有個英文老師July匿名在網路留言板上寫:「香味不是正義,也不該變成道德綁架。」還引來一群人跟風說什麼「香探社=裝文青俱樂部」。
當然也有幫腔的人留言:「我聞到七里香會想寫詩耶!」但在那一串吵鬧留言裡,看起來好像「用鼻子感覺世界」這件事突然變得很不正經。
那一晚,Hy睡不太好。他坐在陽台,看著自己親手種的七里香,在月光下像一群安靜的小士兵一樣站得整整齊齊。他聞了一口,味道還在,但心裡有點不確定了。
是他太多事嗎?只是想聞香,也會惹來麻煩?
第二天他原本想低調一點,甚至想把幾盆移走,但到了校門口,卻看見怡恩穿著圖書股長背心,在門邊發小卡片。
「你幹嘛?」他問。
「發『香探小卡』啊!」她理所當然地說,「上面有我們七里香的插畫,還有一句你的金句。」
他一臉震驚:「我哪來金句?」
她抬手比個剪刀手:「你不是說,『我們需要一種能提醒人記得呼吸的香味』嗎?我幫你印成小卡,超受歡迎耶!」
就在他還想抗議時,一個低年級學妹走過來,笑著對他說:「我放學都會去圖書館門口多聞一口花香,因為這樣我不會那麼怕考試。」
她說完就跑走了,像一陣風。
Hy那一刻突然覺得,鼻子很酸——不是感冒,是一種混著感動跟想哭的奇妙反應。
日子像這樣繼續過著,香探計畫也在不知不覺間滲進更多人的生活。有個原本超討厭花粉的男同學,居然開始試著種沒有花粉的香草;還有一對每天吵架的雙胞胎姐妹,在「氣味盲測」活動裡同時猜對了「媽媽煮飯時的洋蔥味」,然後一起笑成一團,氣氛比任何一次家庭會議都要和諧。
更誇張的是,有天連教育局的人來視察,都被圖書館門口那盆七里香吸引,還對著校長說:「這是什麼品種?很適合做市區綠美化耶。」
那天以後,校長親自來找Hy,語氣半認真半調侃:「香探同學,你要不要寫份提案給市政府啊?」
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沒說好,也沒說不。因為他知道,那代表的是一件更大的事——如果他願意,他的鼻子也許真的可以影響到不只是這個學校,而是整個社區,甚至更多人。
但就在這個時候,一件預料之外的事發生了。
校園外面的一塊空地被公告即將開發,要蓋一間大型停車場。而那塊地,正是Hy跟幾位朋友偷偷種了一整排七里香的地方。
那片地原本是一個廢棄的操場,長滿雜草、垃圾亂丟,沒人管。是他們在假日偷偷清理、鋪上碎石、種上花。現在已經有好幾個附近住戶會帶小孩去那裡玩,還有人在那邊做瑜伽、彈吉他、練呼啦圈。
但現在,一切要被剷掉了。
他坐在那片空地邊的木椅上,看著貼在圍欄上的開發公告,突然有種無力感。那不是只是一片土地而已,那是他聞香以來第一個想主動守護的「世界的小角落」。
「如果我什麼都不做,是不是就真的沒了?」他喃喃說。
第二天,他帶著幾個香探社的同學開始行動。
他們不是去抗議,而是做了一場「氣味告別展」。邀請大家帶著一樣東西——跟那片空地的氣味有關的東西,寫下回憶,擺在場地中間的木箱裡。有人帶了一條毛巾,說是練瑜伽時墊過的;有人帶了一本書,說是曾在那裡看完的第一本小說;甚至有一位阿姨帶來一罐自製的醃蘿蔔,說那是她曾在那邊跟朋友野餐的味道。
Hy則放進了一包土——那是他親手種下七里香的土壤。他聞了一下,那裡還留著淡淡的葉子香味。
那時候三立電視台甚至來採訪了他們。Hy站在攝影機前,有點緊張地說:「我們只是想記住,這裡曾經很香,香到能讓人覺得安心。」
那晚,他回家後收到一則訊息,是Tap傳來的:「你說香味可以被傳遞,那我相信,記憶也可以。」
簡短,但足以讓他落淚。
幾週後,那片地真的被圍起來施工。但在那之前,開發公司竟然主動找上他,說看了報導後很感動,願意保留一小角,設計成「香記憶花園」,還邀他幫忙設計。
他沒有興奮,而是很平靜地點頭,然後說:「我要自己種一棵七里香,放在角落,讓那些還記得味道的人,知道自己來對地方了。」
那之後,他的名字不只在香探社群組裡出現,也出現在市區社區報導、環保青年志工手冊裡。
但他從來不在意這些。
他只在意——那些在生活裡喘不過氣的人,能不能在某個轉角,聞到那麼一點七里香的氣味。
那樣就夠了。
你呢?你視野曾經有過想要主動守護的「世界的小角落」呢?
很多過往曾經去過的地方,並不只是某一片土地而已,而是我們充滿青春回憶的地方。